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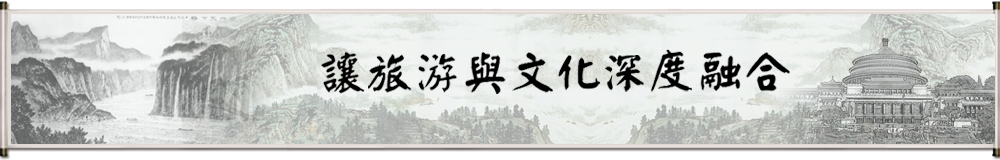
長壽菩提山的名號,既有佛教禪宗文化元素,也有養生長壽文化內涵。如何認知佛教禪宗文化中的養生長壽文化智慧,把佛教文化與養生文化有機結合起來,打造并彰顯長壽菩提山的文化旅游特色,呈現出長壽菩提山的獨家風景,是當前長壽菩提山開發建設中的一篇大文章。基于此,有必要了解佛教禪宗文化中的養生長壽智慧。
佛與壽的孿生緣
提出養生長壽文化與佛教禪宗文化有孿生淵源關系,人們可能會大惑不解。在很多人看來,香火日盛的長壽菩提山,是一個純粹的佛教禪宗文化景區。不過,這個看法并不準確,更不全面。從佛教文化與養生文化的血緣關系上考察,長壽菩提山,既是佛教禪宗文化景區,又是養生長壽文化景區。
也許,在一些人看來,把佛教禪宗文化和養生長壽文化整合于菩提山上,有拉郎配之嫌,顯得十分生硬和勉強。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體系,是有職能分工的,即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也就是說,儒家的學說,主要解決治國平天下;佛家的學說,主要解決人們的心理疾苦;道家的學說,主要解決人們的身體健康。
其實,治心的佛教與治身的道家,就如同人的身與心一樣,兩者密不可分。印度佛教傳中國后,已經不再是原有面目,特別是禪宗的出現,讓印度佛教實現了完全的中國化。中國化的佛教禪宗,自然要包容吸納中國本土的文化,佛教與道家的融合,乃必然趨勢。事實上,中國禪宗從很大程度上,正是印度佛教與中國道家結合的產物。
單就佛教本身而言,把佛教禪宗文化與養生長壽文化,看成是兩個互不搭界的文化體系,甚至認為兩者互不相融,不只是誤解,而且是無知。真正了解佛教的人都有一個共識,佛教禪宗文化與養生長壽文化,是一雙孿生兄弟,乃同一血緣,同一卵生。
眾所周知,佛教是佛祖釋迦牟尼的言教,簡而言之,是指引人類離苦得樂的言教。佛教引導人們離苦得樂,主要方法有讀經、念佛、坐禪等,形成了眾多的門派,至少在唐朝就有八宗之說,其中禪宗就有五家七宗之分。但是,萬殊一本,萬象歸一,離苦得樂的方法歸根到底就是心靈修煉,讓人們掃除世俗塵壤對心靈的垢蔽,認知并回歸本有的清凈之心,獲得智慧的覺悟,重現本有的快樂。
佛教禪宗,注重修心,借助修心而開悟成佛,這個道理稍有佛教常識的人都明白。可是,很多人卻忽略了一個相關的重大問題,即心靈的修養,不只是能夠幫助人們回歸本有的妙明真心而開悟成佛,還能夠有效幫助人們獲得身心的健康,延長生命的周期,達到養生長壽的目的。修心,一因也;開悟與長壽,二果也。這,就是佛教禪宗文化與養生長壽文化的孿生淵源關系。基于此,中國的佛教文化中關節于養生長壽的真知灼見,實在可以看成是提升中國人生命質量的健康寶典。
自古佛門多壽星
佛教禪宗文化與養生長壽文化的孿生緣分,客觀上刺激了佛教養生長壽文化的發展,一個重要的明證是,自古及今的佛門禪林,壽星云集,尤其壽高百歲以上號稱“人瑞”的高僧,可謂比比皆是。
虛云大師,是近代中國著名的佛教禪門泰斗,平生以一衲、一杖、一笠、一鐘,行遍天下,參訪名山,中興多個名寺,由自度而度人,廣利眾生,法德高隆,名滿天下。虛云大師出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9月,經歷了清朝的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和中華民國,圓寂于建國后的1959年10月,世壽120歲。
妙智法師,是虛云大師的弟子,于上世紀30年代末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于虛云老和尚座下。一生慈悲濟世,致力于建寺、印經、雕塑佛像等佛教弘法利生事業和濟困、助學、賑災、助殘、收養棄嬰、放養野生動物、植樹造林等社會公益事業。妙智法師出生于生于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農歷12月28日,圓寂于2003年農歷1月28日,世壽116歲,有“超世豪人”之譽。
本煥和尚,是虛云大師的又一弟子,為臨濟宗第四十四世法脈傳人,出家80余載,募得善款6億余元,先后修建寺院10余座。本煥和尚1907年9月21日生于湖北新洲,2012年4月2日圓寂于廣東深圳,世壽106歲。
虛云大師與妙智法師、本煥禪師,師徒三人,均享奇壽,在中國養生長壽文化史上,堪稱絕世奇觀。
可是,在中國佛教禪宗史上,這樣的奇觀,卻是屢見不鮮,早已有之。唐朝中葉著名的趙州從諗禪師,是禪宗史上一位震古爍今的大師,為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之后的第四代傳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八十高齡的從諗禪師行腳至趙州,駐錫觀音院,弘法傳禪達40年,僧俗共仰,為叢林模范,人稱“趙州古佛”。特別是“吃茶去”的公案,在中國禪宗史上影響極大。趙州和尚出生于唐代宗大歷十三年(778年),圓寂于唐昭宗乾寧四年(897年),世壽120歲。
在中國佛教史上,唐朝以前年齡超過100歲的著名高僧,除禪宗二祖慧可(107歲)、趙州和尚外,至少還有神秀大師(101歲)、惠秀大和尚(100歲)、志鴻大和尚( 108歲)、定安大和尚( 111歲)等。在近當代,除虛云大師和本煥法師、妙智法師三位師徒外,超過100歲的知名高僧,至少還有印順長老(100歲)、禪莊法師(101歲)、凈嚴法師(101歲)、印法和尚(108歲)、通永長老(111歲)、寂勤和尚(100歲)、夢參長老(100歲)、乘清法師(102歲)、圣因法師(100歲)、果章大師(100歲)、圓照法師(103歲)、寂昌大師(103歲)、宏成老和尚(104歲)、離欲上人(124歲)等十多人。
佛教醫學源遠流長
佛門高僧多壽星的現象,固然有多種因素,但佛教醫學的發達,無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佛教有重視醫學的傳統,形成為獨具特色的佛教醫學。從某種意義上看,佛教本身就是一門廣義的醫學,治療的就是人們的各種心病。或許,佛法與佛醫,就是佛教治理人們身心疾病的兩大相輔相成的手段。
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某些文化領域,似乎比中國的起源時間更早。從已知的情況看,釋迦牟尼曾經學習過就醫方明,應該精通醫術。其實,這一點并不奇怪,因為印度本來就是一個醫學發達的國度,佛教醫學,就根植于印度醫學的豐厚土壤。
大約5000多年前,印度就有了相對成熟和發達的醫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醫學體系,當時的名字叫阿育吠陀(Ayurveda)。在印度梵文里,阿育(Ayus),指的是生命;吠陀(Veda),指的是知識或者智慧。阿育吠陀,就是生命的科學。
通過飲食、練習、草藥、按摩以及冥想來等方法,來保持人體內三大生命能量的平衡,是阿育吠陀醫學的基礎。由早期的文獻可看出,阿育吠陀的醫生對于植物的強力醫療特性具有先知灼見,可說是現代藥理學的開山鼻祖。他們也對體內系統的運作極為了解,甚至有證據指出阿育吠陀醫師為患者動過人體手術。阿育吠陀從古到今都同樣強調飲食與靈性的重要性。從古到今,阿育吠陀一直在無數印度傳統家庭中使用著,猶如中國的中醫至今廣為流傳一樣。
阿育吠陀的影響,早已波及南北半球幾乎所有的醫學系統,因此被譽為“醫療之母”。有證據表明阿育吠陀醫學曾豐富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醫學體系。通過與印度的海上貿易,埃及人了解了阿育吠陀醫學。亞歷山大大帝的入侵,使希臘人和羅馬人接觸到阿育吠陀,因而,“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醫療方法,就可見到阿育吠陀的影子。隨著佛教東傳,阿育吠陀醫學也傳播到東方,并對藏醫學和傳統中醫草藥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中醫學還隨處可見佛教醫學的存在。
阿育吠陀對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和傳統中醫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唐朝的義凈法師,曾經通過海路留學印度,回國后所作的《南海寄歸傳》,有二篇文章專論印度醫學。《大藏經》中包含多部佛教醫經譯文,涉藥用動、植物有500余種。除了釋迦牟尼精通醫學外,印度的很多高僧都是精通醫道者,特別是早期到中國來的印度高僧,一般都既能佛法,又兼通醫藥。中國歷代高僧,也不乏佛與醫兼通的醫者。晚近梁平雙桂堂的妙談大師,就以精通醫學聞名。高壽達116歲的虛云大師弟子本煥法師,就精通醫學,并且總結出了“三勤、三靜、三淡、三樂”的養生之道。
佛教醫學對中國傳統醫學的影響由來已久,既深且廣。三國魏明帝時期,就有印度僧人譯出了佛醫經典《醫方明》。從漢代末期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共翻譯了佛典1621部4180卷,其中含有大量的佛教醫學內容。這些醫術理念對中醫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佛教對于中醫的影響,集中表現在醫學書籍的理論總結和醫學家行醫治病的實踐方面。在理論書籍方面,《諸病源流論》和《千金方》都深受佛學的影響。巢元方所著的《諸病源流論》,闡述的人類疾病分為404種,與佛教的病理分類大致相同。被中醫尊為醫圣的孫思邀所著的《千金方》,也曾借鑒了佛教醫學的治病方法,比如,他用佛經中提到的耆婆的醫療手法,有效地治療了許多疑難雜癥,并且借鑒了很多佛教醫學的急救方法。除了利用藥物治療之外,中醫現在仍在使用一些原本為佛醫所用的醫療方法,比如修禪、按摩和行針。
修行的養生功效
人類的很多疾病,追根到底,往往都是凡心里的煩惱引進的。按照佛教的觀點,這些煩惱產生的主要根源是三毒:貪、嗔、癡。貪,主要是指人被財欲、色欲、飲食欲、名欲、睡眠欲等五種欲望所迷,不能自拔。嗔,就是發怒,就是對自己不喜歡的、討厭的東西所產生的情緒。佛家甚至將嗔毒看得比貪毒還重,佛經上有“寧起百千貪心,不起一嗔恚”之說,因為,嗔恚是對別人的憎恨,施加在他人身上危害更大。癡,則是指不明事理,不明人生真相,因而顛倒妄想,產生煩惱,故佛經中強調“諸煩惱生,必由癡故。”
對于治“三毒”,通向涅槃之境,原始佛教提出了系列解決辦法,歸納為“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見,就是要明了佛教一切因緣生、一切因緣滅的道理,了解事物的真相,樹立正確的見解。正思惟,就是心中不存邪念,遠離貪欲、嗔恚、癡念等邪思惟,繼而遠離痛苦,獲得快樂。正語,就是遠離妄語、兩舌(搬弄是非、挑撥離間)、惡口(惡語相加,令他人煩惱)、綺語(巧飾言語,取悅于人)等一切虛妄不實的話語。正業,就是要從事光明正大、正當合法的行為,遠離一切殺生、邪淫等等惡行,以清凈身、口、意三業,遠離惡業。正命,就是以正當的途徑,謀求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必需品,以維系生命。正精進,就是棄惡揚善,精進修行。正念,就是專心致志地默念善法,想念正道,不在思想行為方面犯錯誤。正定,就是收攝各種雜念,離開一切妄想,身心歸于寂靜。究其實質,八正道提倡的是一種正確、正常、健康、有益身心的修行原則。
八正道,后來又歸結為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六種度濟到涅槃彼岸的方法。布施,就是用慈悲心腸對別人施以福利。持戒,就是嚴守盜、殺、淫、妄、酒等戒律,其中戒淫和戒酒,與養生尤其相關。忍辱,要求忍受一切侮辱和痛苦。精進,就是專心致志,不斷進取,絕不半途而廢。禪定,坐禪入定,排除雜念。般若,即認識世界真相后解脫一切煩惱后的大智慧大快樂。
六度,簡而言之,就是佛教修行的精髓戒、定、慧三學。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可由戒學統攝。禪定,相當于定學。般若,就是慧學。戒、定、慧,就是對治貪、嗔、癡的良藥。
從佛教修行角度看,涅槃的境界,要求人們擺脫煩惱,止息欲望,心神集中又心平氣和,這樣的狀態,其實也就是人的身心健康的理想狀態。因此,在佛教徒采用各種方法修行以追求涅槃的過程中,雖然他們的目的在于來世能脫離苦海,往生極樂,但客觀他們修行在今世產生了有益的效果,就是帶來了身心的健康。因此,佛教雖然認為生命短暫,但它在宗教修行中凸現出對生命的重視。
其實,佛教的終極目標涅槃,就是一種純凈清涼的心境。從某種意義上說,佛教就是心的宗教。八正道也好,六度也好,三學也好,都是治心的手段。通過這種有意識的“修心”過程,人的內心世界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寧靜與平和,個人的身心會處于一種和諧的狀態,而這種身心和諧的狀態,就是健康長壽的保證。
心藥治病的妙用
當今,健身訓練、瑜伽功法、按摩理療、氧吧足浴等養生方法層出不窮,各有所長,對人的身心健康確實不無裨益。然而,現代都市人的疲憊和焦慮感,主要來源于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也就是說,當代人的病癥,更多的是心病。俗話說:“心病終需心藥醫”。假如不從內心的休憩靜養出發,而僅僅停留于外在肢體層面的放松和保健,其養生效果其實是十分有限的。
養生之道,首在養心。養生之法,最主要是要卸下人們沉重的心理包袱,將困擾我們內心世界的種種雜念煩惱加以消解,然后才能進一步談到身體的鍛煉和保健。假如內心始終被欲望所占領,為焦慮困惑的陰影所籠罩,那么即使花再多的錢,去健身俱樂部練得滿頭大汗,也是枉然。
除了八正道、六度、戒定慧等修養之道,客觀上帶來人們內心的清凈之外,中國佛教對心藥治心病也有特別的建樹。唐朝無際禪師(石頭和尚)的《心藥方》,就是佛教心藥治心病的經典。
無際禪師,即石頭希遷(700—790年),廣東端州高要(今廣東省高要縣)人。早年赴曹溪,投六祖慧能門下受度為沙彌。慧能逝世后,前往吉州青原山靜居寺,依止先得曹溪心法的青原行思大師,因機辯敏捷,受到器重,時有“眾角雖多,一麟已足”的稱譽。不久,希遷往參曹溪門下的另一位宗匠南岳懷讓,經過一番鍛煉,再回到靜居寺。希遷弟子甚多,禪宗五家中的曹洞宗、云門宗、法眼宗,就是石頭希遷的法系。當時,石頭希遷與另外一位禪門巨匠馬祖道一,合稱二大士。
針對心病流行,無際禪師曾經寫了一篇“致上福上壽”的《心藥方》,專治人們的心病:
凡欲齊家、治國、學道、修身,先須服我十味妙藥,方可成就。
何名十味?慈悲心一片、好肚腸一條、溫柔半兩、道理三分、信行要緊、中直一塊、孝順十分、老實一個、陰騭全用、方便不拘多少。
此藥用寬心鍋內炒,不要焦,不要燥,去火性三分,于平等盆內研碎。三思為末,六波羅蜜為丸,如菩提子大。
每日進三服,不拘時候,用和氣湯送下。果能依此服之,無病不瘥。
切忌言清行濁,利己損人,暗中箭,肚中毒,笑里刀,平地起風波。以上七件,速須戒之。
以前十味,若能全用,可以致上福上壽,成佛作祖。若用其四五味者,亦可滅罪延年,消災免患。各方俱不用,后悔無所補,雖扁鵲盧醫,所謂病在膏肓,亦難療矣;縱禱天地,祝神明,悉徒然哉。
況此方不誤主雇,不費藥金,不勞煎煮,何不服之?
偈曰:此方絕妙合天機,不用盧師扁鵲醫。普勸善男并信女,急須對治莫狐疑。
這個藥方,雖然只有十味藥,但味味都是對癥下藥,都能明心見性。服此藥方,就能消除“貪、嗔、癡”三種病毒,就能擁有一個健康的肌體和一個明凈的心靈,就能成為一個擁有好肚腸,常懷慈悲心,多幾分柔順,明一些事理,對人守信用,對朋友講義禮,對父母孝順,對師長尊敬,誠信不欺,不損陰德,處處給人方便的君子,就必然有一顆平和的清凈心,慈悲的仁愛心,善良的愉悅心,內心深處就能激發出一種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正能量,從而達到養生長壽的目的。
素食的健康價值
素食是我國漢傳佛教飲食文化的核心內容,是佛教養生之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教所謂素食,即不食葷腥。其中的葷,并不是指我們今天所說的大魚大肉這些葷菜,而是指蔥、蒜、韭菜等五種氣味強烈(辛臭)的蔬菜;腥,指一切動物肉。
佛教提倡素食,由來已久,從印度佛教時期已經開始提倡。中國佛教倡導素食,并奠立成為一種必須遵守的制度的,則是梁武帝蕭衍,其《斷酒肉文》是中國佛教史上關于素食的一篇極其重要的珍貴文獻,第一次以制度的形式,對僧尼不食酒肉作了嚴格的規定。自此以后,漢傳佛教僧尼便有了吃素的規定,出家人必須嚴格執行,佛教也提倡在家居士吃素。
佛教徒堅持素食,其養生效果是顯而易見的。素食為什么可以養生呢?這需要用現代科學來解釋。蔬菜水果中含有豐富的營養,容易被人體吸收,豐富的維生素和氨基酸更是人體健康必不可少的元素。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認為蔬菜比葷菜更有益健康的觀點,正被科學研究所證明。
而現代科學家研究表明,葷菜所帶有的高脂肪、高蛋白質、高膽固醇等等的確對人類的健康造成不小的危害。而現代人的高發病如糖尿病、肥胖、動脈硬化、高血壓、癌癥等,也和過多攝入含有高蛋白、高脂肪、高膽固醇的肉類和肉制品有密切關系。
現代科學研究還發現,素食的養生保健作用,很大程度體現在素食的抗病功能上。比如多項研究發現,蕃茄內含的番茄紅素( Lycopene),能夠大幅減少患攝護腺癌等癌癥的機率,在烹煮的過程中,番茄紅素就會自然釋放,生食也很好,是最佳的維生素 C來源。
蔬菜的抗病作用近年來得到充分的重視。蔬菜中所含的豐富天然維生素,能分解淀粉和一氧化碳,可以把體內的廢物排掉。就人體而言,血液應呈微堿性,血液中富有鈣和鉀等礦物質。而動物性的食品多半容易使血液變酸性,而植物性的食品大多含有較多的礦物質,所以素食會使血液變微堿性,有助于身體健康。
從佛教的角度看,由于素食的起因和根本目的在于戒除殺心,徹底改變人性中的兇惡殘暴,培養人性的慈悲。所以在譴責肉食,提倡素食的時候,佛教常常將之與慈悲的觀念聯系起來。《大般涅槃經》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梵綱經》也說:“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佛性種子,一切眾生見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食肉得無量罪。”若然人能夠不殺生,不食肉,保持佛性種子不失,非但兇惡個性變為善良,減少人間互相搏斗,互相殘殺的罪行,還能夠普渡眾生,勸阻殺戮行為的發生,阻止犯罪行為的蔓延,從根本上營造一個和平與和諧的人類社會。
實踐證明,佛教徒常年食素,對他們健康是大有裨益的。歷代高僧大德中,有不少長壽之人,與他們堅持食素有密切的關系。
德高望重的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堅持蔬食長達七十年之久,每日兩菜一湯,飯二兩左右,有詩云:“不知肉味七十年,虛度自漸已九十;客來問我養生方,無他奉告惟蔬食。”趙樸初居士以 93歲高齡往生,充分說明堅持素食者,必然會達到養生的效果。
當代高僧星云法師認為,“素食有益身體健康,而且可以培養耐力,養成溫和的性格。一些吃素食的老和尚,他們每天早起到晚,整天莫不精神奕奕,究竟原因何在?素食最主要的是長養慈悲心,從心靈的凈化來減少瞋怒,達到內心的安然、祥和。”看來,心的平靜、安詳,是養生的根本目的。無論是坐禪也好,修習止觀也好,或是堅持素食也好,一定要首先有一顆安靜的心,才能達到養生的效果。
歷代高僧大德用他們堅持素食的實際行動向我們昭示了佛教素食的養生理念,無論是信仰佛教的人,還是不信仰佛教的人,都應該重視他們的經驗。
茶禪一味的盛行
中國盛產茶葉,中國佛教與茶更是有著不解之緣。飲茶不違反戒律,又可以消除修行中產生的疲勞而提神醒腦,使人神清氣爽,思維清晰,且具有生津止渴、消除疲勞的保健功效,于是乎,茶逐漸成為佛教徒最鐘情的飲料。
北宋后期圓悟克勤禪師提出“茶禪一味”,成為中國禪宗叢林的流行語。茶作為一種飲品,和其味至清至純,與禪家清凈之心十分契合。而茶道與禪道有相通之處,烹茶、飲茶便是在修心養性而參悟禪道乃至保任天機,禪茶一味,洵非虛語。所以飲茶便成為禪宗悟道之機和養生之術。日本禪宗受中國“茶禪一味”的影響,而形成以“和敬清寂”為特征的日本茶道,甚至認為“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這也是禪道的中心。”這樣,汲水拾薪、燒水烹茶、供佛施人、啜飲默坐、插花焚香,皆是習禪修行。
中國的茶文化有一個現象,似乎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中國茶葉中的很多名品,都是由寺廟培植的,即使有些并非原產于寺院,但要跟寺廟、佛教、僧人相結合之后,才得以名重天下。如太湖的碧螺春,最早產于洞庭山水月院;浙江湖州顧渚山的貢茶紫筍,最早產自吉祥寺;君山銀針,產自白鶴寺;龍井茶,產于杭州龍井寺;黃山毛峰,產自云谷寺;大紅袍,出自武夷天山觀;蒙頂云霧,產于四川蒙山智炬寺;松蘿茶,產于徽州松蘿庵等。
茶葉能幫助佛教徒集中精神修煉。《神農本草經》說:“茶葉苦,飲之使人益思,少臥,輕身,明目。”佛教提倡僧人在打坐的間隙飲茶,以休息和提神。比如唐代百丈禪師創《百丈清規》,就規定參禪一炷香后,僧人可以飲茶,稍事休息,稱為“打茶”。唐開元年間,泰山靈巖寺晚間參禪,過午不食,飲茶充饑,以助禪道。佛教徒認為,茶具有“三德”:坐禪時,通夜不眠,茶可以提神;吃飽腹脹時,茶能幫助消化,去除油膩;當性欲躁動時候,茶為“不發之藥”,具有抑制欲望的作用。唐代詩僧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中又有“三飲得道”的說法:“一飲滌昏昧,情思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此物清高世莫知。”現代科學也證明,喝茶能使人記憶力變得更加集中和專注,且具有舒緩神經的作用,能夠讓大腦保持清醒。
茶能幫助佛教徒驅除疾病。唐代陸羽的《茶經》說:“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四肢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明代錢椿年的《茶譜》這樣總結茶的保健去病功效:“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正因為飲茶能使人少生疾病,唐代陳藏器《本草拾遺》干脆稱茶為“萬病之藥”。
茶中所含的茶多酚,能夠極大地有益于人體健康。人體有一種“氧自由基”存在,過量的“氧自由基”誘發了各種致病因子,而茶多酚卻能清除過量的“氧自由基”。人們在日常飲食中,往往吃進致癌物質亞硝酸鹽,這種成份在人體內會合成亞硝胺,促使細胞癌變,而茶多酚的清除“氧自由基”的作用,卻能阻斷亞硝胺在體內合成,因此減少癌變的發生。
茶有如此重要的養生保健作用,無怪乎古往今來,高僧大德們大多重視茶、喜歡茶,乃至于嗜好飲茶。由此,茶與中國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正因為中國佛教徒較早就認識到茶的保健、抗病、提神作用,故而提倡僧人飲茶,茶便與佛教珠聯璧合,融入佛教的發展和佛教徒的日常生活之中,且成為一種特殊的養生長壽之學。
發人深思的四食觀
人的健康長壽,離不開飲食習慣。產生于印度的佛教,作為一種宗教的哲學體系,對人的食欲以及飲食與修行、傳教的關系有著許多獨到的研究和規定。釋迦牟尼為沙彌說十數法,第一句即“一切眾生皆依食住。”這里的住,有生存、安住之義,也就是說,一切眾生必需依食而得生存。
不過,佛教的“食”,并不光指物質形態的飲食,還包括精神領域的飲食,因而將將食從欲望、攝取、執著的角度分為四種,也就是四食。釋迦牟尼告誡大眾:“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也就是說,四食,是佛家的健康長壽之道。
一是段食。指人體由對食物營養及色香味的生理需求而進行的攝取行為,由于飲食有粗細、餐次的不同,因而名為段食。
二是觸食。眾生以眼、耳、鼻、舌、身、意六種官能,即通常所說的六根,去接觸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境界,即通常所說的六塵,由于根境識結合而生起欲樂、適意的感覺,即為觸食。
三是思食。即各種思慮、思考、意欲,使意識活動得以進行,是為思食。
四是識食。與愛欲相應,執著身心為我的潛意識活動,即為識食。
佛教認為,一切有益于人、能令人生起執著、意樂的對象皆可名為食,并將它分為段食、觸食、思食、識食四類,同時指出,一切形式的生命無不依食而生存。這在我國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擴大和深化了我國對“食”的認識。
佛教的四食,一個比一個細,后三種食基,本屬于精神活動范疇。佛教通過這種劃分,將“食”的概念擴展到精神領域,認為一切能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求的東西都可稱為食,它直接增益著有情眾生的現前生命,同時關系著未來生命的再創。如《俱舍論疏》卷一說:“寒過日光,即值炎火,熱逢樹影,并得風涼。有益于人,皆名為食。”《雜阿含經》卷三三說:“若于四食,無貪無喜,無貪無喜故……于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不起。于四食有貪有喜,則有憂悲有塵垢……。”
可見,佛教認為“食”是眾生生死癥結的根本問題之一,若調適不當則不能與道相應。當年釋迦牟尼佛在雪山修苦行六年,有時一日僅食一粟一麥,餓得骨瘦如柴,卻始終未能與解脫境界相應。于是放棄苦行,接受牧牛女供養的奶酪,身體得到資益,于菩提樹下很快進入禪定境界,終于在臘月初八日晨睹明星而悟道。可見適當的食物和營養對禪修的重要。后世佛教徒為了紀念釋迦佛的成道日,每年臘月初八都要熬粥供眾,稱為“臘八粥”。
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四食的提法,改變了我們對飲食的觀念。從養生長壽角度看,影響人們健康長壽的“食”,不只是物質的飲食,還包括人的感官所能感知的色、聲、香、味、觸、法等等外部世界,包括人們思考牽掛的一切事情,包括個人的潛意識活動。這些東西,都是影響生命周期的“食”。這就提醒人們,要相健康長壽,必須從物質和精神兩個領域,控制好“食”的問題。這對人類而言,無疑是極具啟發作用的養生觀。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