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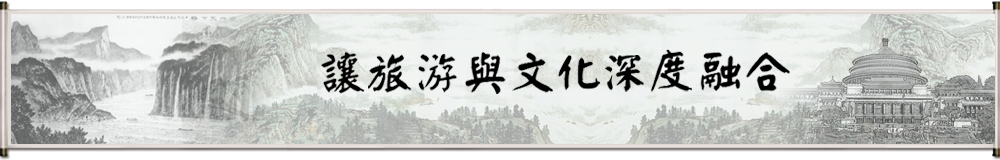
福村,一方遠離塵囂的凈地,草創之中就名聲在外。
奇怪,我不曾一睹她的容顏,但一聽這個名字,就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心追之,目望之,神游之。
福村的創意,少不了遠山如屏,清溪亂流,樹影婆娑,月色清涼,蛙聲四起,稻香橫溢,雞鳴犬吠,炊煙農舍……。福村既然叫村,當然會有這些亙古不變的招牌元素。
可是,我心里的福村卻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些久為人們心向往之的田園風物,轉瞬之間消隱于蒼煙落照之中,幻化成詩人筆下的一片詩意,畫家胸中的一抹畫意,禪者臉際的一段禪意。
因為,聽完福村的描述,我腦海里竟忽然蹦出四個字:隱逸是福。
隱逸是福,有違常理。在中國,不幸則隱,早已成為一種思維定勢和行為習慣。恥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騎牛西去的老子,箕踞鼓盆而歌的莊周,祼游狂飲的竹林七賢,種豆南山下的陶淵明,埋名石船山的王夫之,這些隱逸高士,哪一個不是失意者。
我為什么作如是想,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許,是那些鑲嵌在大自然中的詩畫意趣勾起了我對古人生活圖景的神往。也許,是那些為人津津樂道的靈山異水激起了我對故鄉的懷思。也許,是我早已厭倦了喧鬧,潛意識里一直在尋找一個讓心靈歇息的地方。
隱逸是福,這是囈語,怪論,還是洞見,妙解,我自己也無法一時做出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一定是福村的出現,撞擊了我的某扇心靈之門,觸動了我的某根敏感神經,激活了我的某種蟄伏的意念。
隱逸與福,相反而相成,貌殊而神合。慢慢地,我若有所悟,企圖自圓其說。
什么是福?好多人都能怡然心會,但若要一句話回答,恐怕就有“妙處難與君說”的感嘆。其實,“福”字的長相已經給人們提供了詮釋。左邊的“示”旁,表明與祭祀有關,在古人看來,福是上帝或祖先賜予的。右邊的“一口田”, “一口”表示頭部,“田”象征肚子已飽。通俗地講,肚子脹鼓鼓,心頭美滋滋,就是福。由此引申開來,人的需求得到滿足而心情愉悅的狀態,就是福。
福,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終極需求,其快樂的本質屬性具有唯一性,但表現形式卻千姿百態。
其實,隱逸與福對立中有統一,其統一的粘合劑就是人的需求。按照馬斯洛的觀點,隱逸當屬人類需求的最高層次,因為,隱逸告別的是現實的痛苦,得到的是靈魂的慰藉,追求的是一種自我實現。
當然,隱逸并非簡單的小隱隱于山林,大隱隱于市朝,更非逃避現實,自命高潔的虛榮。在我看來,隱逸在內不在外,在心不在形,在神不在貌。隱逸是掙脫名韁利繩后的心靈恬靜,精神快意,思想逍遙。隱逸是名利的清醒劑,尤其是對那些滾滾紅塵中的奔忙者。
讓心靈隱逸,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無不是福。也許,這并不是福村創辦的初衷。但能讓我對隱逸有所感悟,卻不能不感激福村。
2009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