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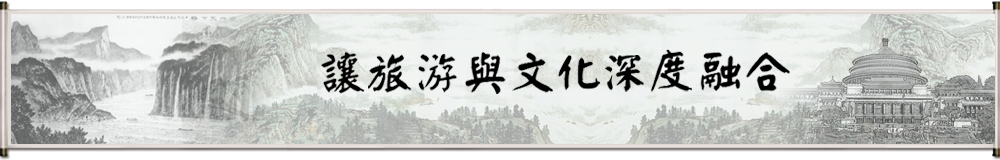
翻開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讀者立即會被撲面而來的愛情氛圍所熏染和吸引。與先秦時期那些傳諸后世的經典著作大異其趣的是,《詩經》的開篇之作,不是學術思想的爭鳴,不是處世之道的訓示,不是治國良策的辯論,不是歷史事件的敘述,而是一幅“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國風?周南?關雎》)的愛情畫面,讓人情不自禁地要誦讀之、弦歌之、舞蹈之、陶醉之、向往之。
的確,愛情詩是《詩經》的主題,《詩經》因愛情詩而大放異彩。盡管《詩經》的名篇佳作不少,但真正讓人們百讀不厭且津津樂道的,還是那些天真活潑、無拘無束、帶頭濃濃鄉里韻味的愛情詩。《詩經·邶風·靜女》,就是其中廣受好評的代表作品。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這首愛情詩,屬于《邶風》,即西周時期邶國地區的作品。這邶國地區,可是一個愛情浪漫、愛情詩發達的地區。邶國,是西周的諸侯國。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滅商之后,為了安置殷商遺民,將商朝王畿之地分為邶、鄘、衛三地,封六弟蔡叔于殷地(今河南安陽),稱邶國,商紂王的兒子武庚也安置于此。邶國的管轄范圍,相當于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帶。但周武王去世后,其子周成王繼位,其弟周公旦攝政。周公平定了著名的“管蔡之亂”,邶國的封號被取消,領地全部劃歸衛國管轄。
由此可見,邶國的都城,就是當年殷商的國都,后來邶國疆域劃歸衛國管轄,仍然屬于當年殷商的王畿地區。處于這樣一個首善之區,邶國的經濟富庶、文化發達,自然遠非其它地區可比,隨之而來的思想開明、生活開放,也遠駕乎其它地區之上,愛情故事的浪漫,更是執全國之牛耳。
從《詩經》收錄的作品看,邶國和衛國的詩歌,愛情主題的作品所占比例相當高,而且名篇名句,俯拾即是。如《邶風》的“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柏舟》);“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擊鼓》)等等。又如《衛風》的“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奧》);“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氓》);“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伯兮》);“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河廣》)等等。可以說,邶國和衛國的愛情詩,代表了《詩經》愛情詩的最高水準。
《詩經·邶風·靜女》,敘述的是一個男女幽會的愛情故事。全詩文字淺顯,完全口語化,但是有情節,有畫面,既有純樸之風,更有真摯之情,顯得淺而有致,淡而有味,令人回味無窮。
第一段,寫男女預約和幽會的過程。靜女,是詩中的女主角。靜,寫女子意態的嫻雅安詳,著眼于女子的性情和修養。其姝,是贊揚女子容貌非凡。其,是形容詞的詞頭,沒有實際意義,但卻有加強語氣的作用,表示確實、硬是如此。姝,音shū,容貌姣美。“靜女其姝”四個字,飽含著男子對女子的贊美和認可。“靜女”的稱謂,已經反映出男子對女子性情修養的認可;“其姝”的敘述,顯然表達了男子對女子長相的愛慕。“俟我于城隅”,寫女子主動等待男子約會,并明確了幽會的地點。俟,音sì,等待。我,男子自稱。于,表示地點位置的介詞,相當于“在”。城隅,一般解作城角,似欠準確。城,非指今天的城市,而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高墻,離城市中心區有一段距離。隅,城墻轉彎的角落處,在一般視線范圍之外,有一定隱蔽性。結合第三段“自牧饋荑”的“牧”字看,城隅所在,應該在城墻的外側,即郊外的牧野,植被甚好,且為放牧之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寫女子假意爽約而考驗男子,男子一往情深而徘徊等候。愛,通“薆”,音ài,隱藏也。見,音xiàn,現身。搔首,以手搔頭,表示焦急或有所思的樣子。踟躕,音chíchú,心中猶疑,要走不走,此處當指來回徘徊,四處尋找。這四句詩,寫預約和幽會的過程,非常簡約,但卻寫得非常到位。靜而姝,女子的德性容顏,可以想象。俟我,說明女子先到約會地點,顯得比較主動。愛而不見,說明女子不僅是靜而姝,而且還有幾分頑皮,顯得聰明機智,有意藏而不露,觀察考驗男子。搔首踟躕,寫男子用情深摯,耐心尋覓,有不見不散的定力。
第二段,寫城隅之會,兩情相悅,女子饋贈彤管一枝作為信物,男子對彤管珍愛備至。孌,音luán,與姝同義,指容貌美好。貽,音yí,贈送。彤管,有多種解釋,今無確解,一說是古代女史用以記事的桿身漆朱的筆;一說指樂器;一說指植物初生的紅色管狀莖干。結合第三段“自牧饋荑”之“牧”字為郊外牧野,“荑”為茅草嫩芽的情況考察,彤管,當是初生茅草的管狀紅色莖干,可作口吹之土制樂器,因當今農村還保留著這樣的樂器形式。有煒,是說彤管的外表紅潤光亮。有,形容詞詞頭,不可解釋為“有無“的“有”,但有加強語氣的作用。說懌,內心喜愛。說,通“悅”,喜悅之意。懌,音yì,喜愛。女,通“汝”,指彤管,此處用以物代人手法,實指靜女。美,是對彤管的評價,實為對靜女的總結性贊美。
第三段,對幽會的信物彤管大加贊美,連續用了三個“美”字,幾乎贊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并揭示出對彤管的贊美愛慕,是基于對靜女的贊美愛慕。“自牧歸荑”,是指在郊外幽會時女子贈給男子的彤管。自,此處作為表示地點位置的介詞,相當于“在”。歸,通“饋”,贈送。荑,音tí,即彤管,是從構成彤管的材料角度說的。“洵美且異”,是贊美女子贈送的信物彤管,確確實實很美好,而且美得異乎尋常,不同凡響。洵美,確實美好,表示十分肯定的語氣,這是承接第二段“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而對彤管之“美”做出的再次確認和強調。“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是一句揭秘性的話,前面對彤管、荑的大量贊美,其實都是在作鋪墊,最終說明之所以對彤管、荑珍愛有加,主要因為它是靜女的化身,是戀愛的信物,是愛情的標記,是走向婚姻的誓言。匪,通“非”。女,通“汝”,指彤管和荑。美人,指靜而姝的意中人。貽,贈送。
在對這篇作品的內容做了大致解讀之后,還有必要對其寫作手法做出簡單的分析。從詩歌藝術看,這首詩大概有五點值得借鑒。一曰懸念的設置。首段交待“俟我于城隅”,按照邏輯必然會順利見面,可突然來了個“愛而不見”,讓讀者頓生心理落差,并想探個究竟。二、三段對彤管和荑贊美不已,最后才解密是“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再次讓人意想不到。這樣的懸念設置,往往有引人入勝之功。二曰情感的遞進。全詩內容依章分層,從約會時的“搔首踟躕”,到約會中的“貽我彤管”,再到約會后回憶和贊嘆“自牧歸荑,洵美且異”,逐層深入,漸到高潮。三曰人物的刻畫。“愛而不見”,女主人公機靈刁鉆的形象真是呼之欲出;“搔首踟躕”,男主人公的憨厚誠實可謂淋漓盡致。四曰留白的妙用。全詩就寫了城隅幽會、彤管相贈和別后相思三個內容,別的完全沒有交待。首段寫幽會,也只寫了“俟我”和“愛而不見”兩個情節,至于如何約會、見面沒有、細節怎樣,則一點沒有涉及,完全留給讀者去想象。二段寫見面過程,只提到“貽我彤管”,本來幽會過程肯定是十分精彩的,可是這些情節全被作者無情地剪掉了。五曰語言的考究。全詩語言淺白,卻有十分講究。靜女的“靜”,其姝的“姝”,其孌的“孌”,彤管的“彤”,有煒的“煒”,洵美的“洵”,特別是四個“美”的反復運用,都是經過了反復推敲的。全詩僅僅五十個字,明明精雕細琢,但卻淺白如水,看似淺白如水,卻又韻味無窮,且裝載的信息量相當豐富,可以給人很大的想象空間。這樣的文字考究功夫,匠心獨具,極見功力,確實值得后來的文學創作者琢磨、汲取和借鑒。
2015年2月7日
|